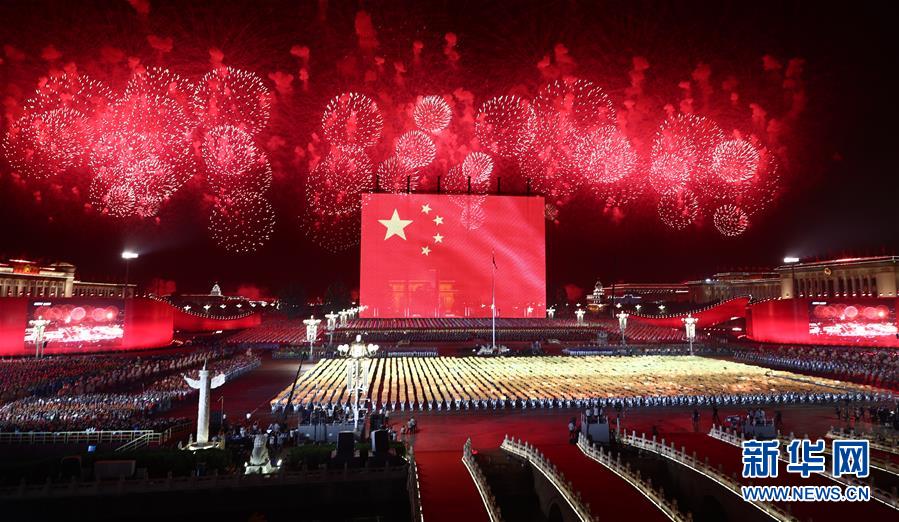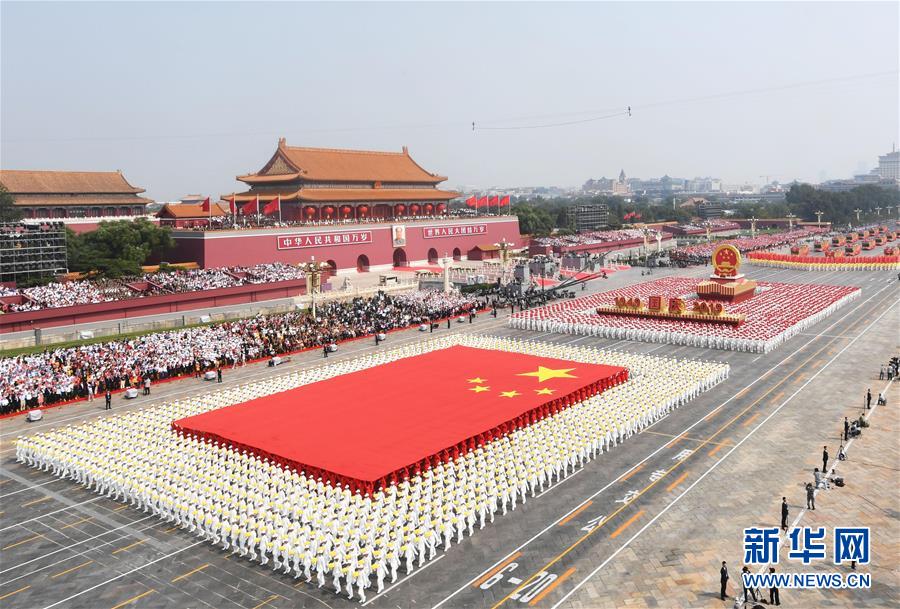原标题:“无人无路无图”,也要寻找长江“出生地”
从1976年起,江源科考队12次综合考察,逐步揭开江源的神秘面纱

8月8日,长江科学院科考车队在途中行进。

8月8日,长江科学院高志扬与同伴们正在吃午饭。

8月8日,长江科学院任斐鹏(右)与袁喆在牙哥峡识别物种类型。

8月8日,长江科学院李伟在采集鱼类样品。本组照片由本报记者吴刚摄
在青藏高原冬季零下35摄氏度气温下,长江源头河流“连底冻”后,鱼群如何过冬生息?
不久前刚结束的长江江源科考发现,以裂腹鱼为代表的高原鱼类,冬季都会选择在温泉附近越冬;同时初步掌握高原鱼类产卵场、索饵场相应生态环境特征。这将有助于加强对江源鱼类的物种保护,应用于自然灾害应对与生态系统修复。
深入“第三极”,探秘长江源。上世纪70年代首次长江江源科考,探明长江源头,确定长江长度“世界第三”。近年来展开全方位、常态化考察,探寻江源生态环境奥秘,江源科考已成为针对长江之源开展次数最多、覆盖最广的科研行动。
2019年江源科考中,20多名科考队员在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江源腹地,累计行程近4000公里。此次科考对长江正源沱沱河、南源当曲、北源楚玛尔河和澜沧江源19个科考点的水资源和生态状况开展综合考察,包括水文、泥沙含量、河道河势、水土流失、地形地貌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宝贵的科考成果。
经历从走进江源、研究江源,到保护江源,江源科考正在逐步揭开江源神秘面纱,为问诊江源展开“体检”。
走进江源:“不到江源心不死”
绝大部分队员都是首次上高原遇到高寒缺氧环境,但江源科考精神引领队员们克服重重困难、开展考察试验
雪山冷峻,荒原苍凉。
一块刻有“长江南源当曲科学考察纪念”的大理石碑,立在青藏高原腹地青海省杂多县阿多乡扎西格君的山坡上。
这是1976年首次对长江源头开展实地考察以来,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展的第12次综合性考察。10多名江源科考队员,向纪念碑敬献哈达,列队致敬,纪念历次长江江源科考的前辈。
“不到江源心不死,死在江源心也甘。”这是43年前新中国首次组织对长江源头展开科考,参与队员签名写下的“决心书”。
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究竟发源于哪儿,当年一直众说纷纭。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现为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说,一个国家如果对自己的重要山川江河最基本的情况都弄不清楚,不仅不足以言现代化,更不足以与之谈开拓创新精神。
1975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以出版《长江》画册为契机,组织力量探明江源。以当时的环境,江源科考可谓困难重重、险象环生。
缺乏查勘测绘,青藏公路以西的高原腹地在地图上长期都是空白区;教科书上长江源头也只能以可可西里山东麓或祖尔肯乌拉山北麓模糊代替;全国各地党政机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市场物资匮乏,更遑论高原探险专业装备保障。
首次江源科考牵头者成绶台回忆,到终年积雪、“无人无路无图”的高原地区去探明江源,当时唯有依靠从国外购置的几张卫星图片判断江源大致方位,“以及国家登山队支援的10多顶登山帐篷和20多套鸭绒睡袋”。
在军队保障支持下,由24名队员组成的科考队在1976年7月开始向江源进发。绝大部分队员都是首次上高原遇到高寒缺氧环境,严重的高原反应让队员头痛欲裂,甚至吐血不止;没有成形道路,卡车经常陷入沼泽,260公里车程要走8天。
坐车、骑马、徒步,在高原走走停停,不断修正路线中行进一个月后,科考队终于抵达沱沱河源头——各拉丹冬雪山。
“卫星图片上江源地区白雪茫茫,模糊一片,沱沱河就像一条黑线。”首批登上雪山的科考队员石铭鼎回忆,登上长江之源的雪山看到,南北侧两条10多公里长的冰川,犹如两条“玉龙”钳状环绕,激动之下不禁对自己低语:“长江,终于找到你出生的地方了”。
经过实地考察与专业测量后,首次江源科考成果在1978年1月由新华社向世界宣布:长江的源头不在巴颜喀拉山南麓,而是在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西南侧的沱沱河;长江全长不止5800公里,而是6300公里,比美国密西西比河还要长,仅次于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和非洲的尼罗河。
这一科考成果震惊世界!
确定沱沱河正源,探明长江南源北源,考察江源水生态水环境,分析高原河床形态……在“勇于挑战、志于科学”的江源科考精神传承中,一代代科考人忍受高原反应,走进江源探索,逐步搭建起科考次数最多、覆盖最全的江源科考体系。
尽管科考条件、后勤保障已大为改善,但江源科考依旧风险不断:在江源河谷中遭遇泥石流,险些被巨石砸中;钻取冰芯花费大量时间,被迫深夜驱车翻越山脊冰川;科考过程中有队员感冒发烧却不愿被送下山,高原上找不到诊所,只好私下架起吊瓶自己右手给左手扎针。
多次参加科考的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副院长陈进说,“不到江源心不死”的江源科考精气神,引领队员们克服重重困难,踏访江源开展考察试验,为系统认识江源、保护江源奠定扎实基础。
研究江源:“逐步揭开神秘面纱”
由于长期人烟罕至、基础数据匮乏,江源地区还有太多奥秘、空白,值得科研工作者前往探索,为之奋斗终生
通天河,因远处源头常被云雾笼罩,形成天上河水倾流入江的壮观景象而得名。
但很多人不知道,在通天河汇聚的长江三源,江水颜色与河势截然不同。
正源沱沱河源起冰川,水流湍急,水色浑浊土黄,犹如藏族康巴汉子;南源当曲支流众多,水量充沛,河水清澈温婉,好比藏族少女;北源楚玛尔河,源起可可西里,流经地势高亢,河水呈现红色,如同神秘的藏族喇嘛。
长江科学院水环境所副总工程师赵良元连续多年参加江源科考。踏上江源,带着仪器设备,采集河流水样、底质、土壤,分析每处采样点的水质现状与水化学特征,这是他科考工作的常态。
“研究分析发现,正源沱沱河发源各拉丹冬,江水主要以冰川融水补给为主,江水中携带大量泥沙,较为浑浊。”赵良元介绍,南源当曲径流以降水、冰雪融水及地下水补给为主,经过大量湿地调蓄过滤,河水清澈。楚玛尔河流经含铁丰富的岩层,河水偏红色。
如同三源河水的巨大差异,江源地区绮丽壮观的自然风光、独特丰富的多样生物、一日四季的气候特点、复杂密布的水系分布,背后都是一串串奥秘,需要科研工作者在江源实地考察、探寻才能得知背后的密码。
“长江江源具有重要的科研、生态、文化价值。”赵良元说,长江源头的高原冰川、湿地,生物多样性突出、河道类型丰富、藏区文化璀璨,吸引大量科研人员前来开展科学考察,探秘长江源。
近年来,长江之源治理水土流失情况如何?江源河流河床为何经常摆动?高原植物群落分布有哪些特征?高原鱼类如何繁衍生息?
围绕这些涉及江源水生态水环境等问题,从2012年开始,长江委每年以“综合科考+专项科考”方式,组织一批批科研工作者忍受高原反应,冒着生命危险,上高原,赴江源,开展实地考察与科研实验。
在海拔超过5000米的采样点,任斐鹏和队友一起费力爬上近百米高的山坡后,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布设样方打桩取样,以便分析江源植被分布以及土壤特点。
我国北方广大草原主要是以耐旱的针茅、羊草等禾本科植物为优势种。这些植物多能生长至50厘米以上,因此能出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
长江源区的高寒草甸则以高原嵩草和矮嵩草等抗寒、耐旱的莎草科植物为优势种,植株通常比较矮小,普遍低于20厘米。同时,由于长江源区地处高原,气候寒冷,植物的生长期也相对更短,一般5月底才返青,8月底逐渐变黄。
“如果将流域生态系统比作一个人体,那么生长在表层的植被就像人体的毛发,而土壤如同人体的肌肤。”任斐鹏说,能为江源地区广大生物提供食物与栖息地的植被与土壤要素,因处于地球表层,对外界环境变化十分敏感。
连续5年参加江源科考后,任斐鹏发现当高寒草甸上莎草、嵩草植物密度下降,菊科、豆科植物增加时,成为草甸土壤退化的重要标志。
不到两年时间内,科考队员李伟连续第5次进入江源观测高原鱼类特性。每次,他都穿上防水服、扛上渔网与设备,在冰冷河水中捕鱼、采样。他说:“处于水生态系统食物链顶端的鱼类,是水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江源水生态系统安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每次科考,李伟几乎都会遭遇不同的坎坷:茫茫大雪中车辆“趴窝”,脚被鞋里的大木蜂蜇伤,在零下30℃的当曲南源野外过夜。就在他快熬不住时,最终发现高原鱼群在冰天雪地中选择越冬场、产卵场、索饵场的奥秘。
“定位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位置,掌握关键栖息地的水文水动力特征,对于开展高原鱼类人工繁殖和增殖放流具有重要价值。”李伟介绍,实现人工繁殖后,一旦出现灾害性事件影响鱼类繁衍生息,就能通过增殖放流尽快对受影响河段进行种群恢复。
一项项冒着风险、忍受寂寞,最终不期而遇的发现,正逐步解开江源的神秘面纱。
长江科学院副总工程师徐平说,上百人次参与、累计行程过30万公里的历次江源科考,不仅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江源科研数据,多次获批纳入国家科研基金项目或国家重点研发课题,“更重要的是培养出了一支有志于江源研究的青年科考队伍”。
与平原河流河床相对稳定相比,江源地区河流河床却经常出现“摆动”,由此呈现各类辫状、分叉等形态。河床的不稳定,造成江源地区桥梁桥墩、临河道路极易破损,使用寿命很短。
“桥墩、路基经常遭遇河水冲刷,容易被掏空。”长江科学院枢纽泥沙研究室主任周银军介绍,平原地区都会根据相应冲刷公式测算,采取对应防护措施。由于江源地区河流河床与岸坡之间泥沙交换频率特别高,这些公式在江源地区不适用,常规防护措施很难收效。
从2014年开始,周银军和团队一起七上江源。在冰天雪地中,住帐篷、啃馒头,在不同河段打孔取样,首次使用数字技术成功还原出江源河流断面历史形态,为后续研究推断高原河流冲刷公式奠定基础。
80后的周银军由此成为江源河床科研中的佼佼者。他说:“由于长期人烟罕至、基础数据匮乏,江源地区还有太多奥秘、空白,值得科研工作者前往探索,为之奋斗终生。”
保护江源:“让江源永葆生机”
江源科考,经历了“走进江源、研究江源、保护江源”三个阶段,已经从一项综合考察全面转变为保护江源的执着坚守
江源地区绮丽的风光、壮观的景象背后,是极其敏感脆弱的生态系统。科考发现,江源地区生态系统整体保持良好状态,但面临的挑战与影响不容小觑:
气候变化。青海水文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1956年至2016年间,江源地区平均气温上升了1.7摄氏度,上升倾向率为0.33℃每10年,年平均气温上升显著;年降水量增加了65毫米,增加速率10.2毫米每10年。气温影响源区内广布的冰川积雪融化,导致雪线上升,冰川后退;降水和气温等因素进而影响径流过程,沱沱河、直门达径流上升趋势明显,变化倾向率分别为1.1亿立方米每10年、5.7亿立方米每10年。
土壤退化。高寒草甸及土壤附着在高原高寒冻土之上,形成时间异常漫长。如果平原地区形成1厘米土壤需要100年,江源地区则需要200年以上。局部地区高原草甸出现明显退化,甚至呈现沙化趋势,生物多样性下降,地表植被覆盖度减少,生态调节功能削弱。
科考队员孙宝洋博士介绍,如果植被干扰、土地退化等形势得不到及时扭转,江源地区水土流失或将进一步加剧,长江江水含沙量也将明显增加,当地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将会恶化,局部地区甚至有变成戈壁滩的风险。
人类活动。长江江源水温要比中下游低十几摄氏度。赵良元表示,长江源区地处青藏高原,气温普遍偏低,水温一般不会超过10摄氏度,“水温较低也意味着水体自净能力较弱,污染物降解过程也相对缓慢。”
随着高原地区城镇化,加上修桥筑路以及放牧养殖,给江源生态带来的影响日益明显。科考发现,江源部分河段水体中的碳、氮、磷含量相对较高,甚至出现大量青苔,这或与江源地区牧民放牧粪便堆积、生活垃圾堆放等污染密切相关。
“水生态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上就有水生态被破坏,造成文明消亡的‘楼兰古国’教训。”长江科学院党委书记吴志广说,江源地区以水生态为主的问题挑战,表面上看是区域性问题,但实际上“牵一发而动全身”。
长江大保护,从江源开始。
受冰川消融、降雨增加以及上游卓乃湖溃堤等因素影响,位于可可西里腹地的盐湖近年来水位不断提升、面积持续扩大。长江科学院空间所在江源科考中发现,这个咸水湖面积从2011年的40多平方公里,8年间猛增到超过200平方公里,水位一年间最高涨了4米。
不断扩大的湖面,不仅破坏湖边草地生态环境,还直接逼近青藏公路与青藏铁路。科考队员文雄飞近两年来10多次进入可可西里,观测盐湖水域面积与水位,使用无人机拍摄分析盐湖周边地形、水网数据,测算确定实施盐湖引流的最佳隘口。
“江源是人类共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宝库。”文雄飞感言,能用科考积累的数据与专业分析测算,为可可西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是参与江源科考最大的收获。
建立江源科考基地对江源水资源及生态环境开展持续观测实验,开展唐古拉山冬克玛底冰川及小流域气象水文观测,系统研究公路建设对高原草甸湿地水生态影响,规划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文水生态观测站网……
高原草甸十分脆弱,队员们取样时尽量减少取量;研究江源鱼类时,捕捞的江鱼经过测量后尽量放生;遇到游客遗留的塑料袋与垃圾,都会主动收集回收处理;有着保护鱼类习俗的藏区群众,从怀疑队员“滥捕”,到主动反映情况,相互结下深厚感情……
“科考江源持续多年,除了一点点积累河流的基本资料外,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人们保护江源的意识越来越强。”科考队员闫霞说,与此同时,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江源生态环境和河流管理保护工作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这激励我们科研工作者不断去研究,提出适应性保护策略。”
在前期科考数据基础上,江源科考队还将结合现有考察结果,对照历史资料数据,对江源水生态水环境开展全方位“体检”,直观反映当前风险挑战,并科学地提出保护建议。江源科考,从一项研究江源的综合考察,全面转变为保护江源的执着坚守。
“江源科考目前已经历了‘走进江源、研究江源、保护江源’三个阶段。”吴志广表示,上世纪70年代的江源科考,主要是探明长江源头;近年来的多次江源科考,重在采集江源冰川、水土、生物等相关数据,全面系统认识江源的整体情况;去年以来的江源科考,则是比对历年科考数据,对江源开展“体检”,更好地保护长江江源。
吴志广说,走进江源、研究江源,最终目的还是保护江源。希望通过科考探索,增强各界“保护江源,敬畏江源”意识,让江源江水奔流不息,让长江永葆生机活力。(记者李劲峰、李思远、吴刚)
大视窗
新闻热点
新闻聚焦